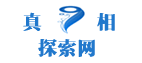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7月13日报道,在2021年疫情期间某个安静的午后,当时还是美国赖斯大学研究生的王志远(音)正在通过求解一个古怪的数学题排遣自己的无聊。在找到一个奇特的解法后,他开始畅想这道数学题是否可以用物理学加以诠释。最后,他意识到这道题似乎是在描述某种新型粒子:它们既非物质粒子、也非力传递粒子。它们似乎是某种完全不同的粒子。王志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意外发现发展为关于这种第三类粒子的完整理论。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导师卡登·哈泽德。哈泽德回忆说:“我当时对他说,我不敢肯定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你真的认为事实就是如此,那么你应该把全部时间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停掉你正在进行的其他所有研究。”
目前已是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的王志远与哈泽德今年1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经过优化的研究结果。他们声称,被称为仲粒子的第三类粒子可能确实存在,而且这些粒子可以生成奇异的新物质。
当该论文发表时,维也纳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所的物理学家马库斯·米勒也已因为别的原因正在思考仲粒子的概念。根据量子力学,目标和观察者在同一时间可以处在多个位置。米勒当时思考的是如何在理论上实现处于这些共存现实“分支”中的观察者视角之间的切换。他意识到这会对仲粒子存在的可能性增加新的限制,他的团队今年2月在一篇预印本论文中介绍了研究结果,该论文目前正在接受某学术期刊的审稿以便公开发表。
两篇论文写作时间的相近纯属巧合。但总体而言,这项研究正在重新打开一个曾被认为在数十年前已得到解决的物理学谜题的卷宗。一个基本问题将被重新评估:我们的世界可以有哪几种类型的粒子?
隐秘世界
所有已知的基本粒子分成两类,它们的行为截然相反:构成物质的费米子和传递基本作用力的玻色子。
费米子的决定性特征表现为:如果你调换两个费米子的位置,它们的量子态将增加一个负号。这个不起眼的负号具有重大意义——意味在同一时间、同一位置不可能存在两个费米子。当挤压在一起时,费米子的压缩程度存在某个极限。这一特性阻止物质发生自我坍缩——这也是每个原子中的电子存在“壳层”结构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个负号,我们人类就不可能存在。
玻色子则没有这样的限制。成群的玻色子可以相安无事地做完全相同的事情。例如,任意数目的光子可以处在同一位置,这一特性可以制造出激光器。激光器在同一时间发射出大量完全相同的光粒子。这种能力归结为这样的事实:两个玻色子调换位置时,它们的量子态将保持不变。
费米子和玻色子未必是仅有的两个选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量子理论的基本特性:要想计算表示某个粒子处于任何特定状态的概率,你得把该量子态的数学描述进行自乘。这个步骤将抹掉差异。例如负号将消失。如果提问者给出的数字是4,那么美国《危险边缘》电视智力抢答节目的选手将无法知道问题要问的是“2的平方”还是“-2的平方”?这两种可能性在数学上都成立。
正是因为这一特性,费米子尽管在对调位置时获得了负号,但它们在被测量时看起来完全相同——因为当量子态进行平方运算时,这个负号将会消失。这种不可区分性是基本粒子的关键属性:没有任何实验可以区分同类型的两个粒子。
1925年,25岁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提出了“不相容原理”:两个无法区分的费米子决不可能具有相同的量子态。
但是负号也许并非唯一消失的东西。在理论上,量子粒子还可能隐藏内部状态,即在直接测量中无法观察到的数学结构,它们也会在量子态平方运算时消失。当这些粒子调换位置时,从这种以无数种方式变化的内部状态中可能出现第三类更为普遍的粒子,即所谓的仲粒子。
尽管量子理论似乎认可这一假设,但物理学家一直难以找到关于仲粒子的有效数学描述。20世纪50年代,物理学家赫伯特·格林曾进行过一些尝试,但进一步的检视发现这些仲粒子模型实际上只是典型的玻色子和费米子的数学组合。
20世纪70年代,正确的仲粒子模型缺失之谜似乎得到了解决。一组被称为DHR理论——以数学物理学家塞尔吉奥·多普利凯尔、鲁道夫·哈格和约翰·罗伯茨三人姓氏的首字母命名的定理证明,如果某些假定成立,那么只有玻色子和费米子存在物理上的可能性。其中一个假定是“局域性”,即认为目标只能受其邻近事物的影响。(用哈泽德的话解释:“如果我挪动桌子,我多半不会立刻影响月球。”)DHR论证还假定宇宙(至少)是三维的。
这些结论在几十年里阻止了对仲粒子的研究,只有一个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物理学家弗兰克·维尔切克提出了“任意子”理论,即一种既无法描述为玻色子也无法描述为费米子的粒子。为了绕过DHR定理,任意子存在一个重大局限:它们只能存在于二维空间。
今天物理学家对任意子进行广泛研究以探索它们在量子计算中的潜力。即便局限于二维空间,但它们仍可呈现在某种材料的平坦表面上,或者量子计算机的二维量子比特阵列中。
但是,可以形成固体的三维仲粒子看来仍然不可能存在——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调整目标
在构建他们的模型时,王志远和哈泽德注意到DHR理论背后的假设超出了常规的局域性担忧。哈泽德说:“我认为人们过度解读了这些定理真正施加的限制或约束。”他们意识到,归根到底,仲粒子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的。
在他们的模型中,除电荷、自旋等粒子的常见属性外,仲粒子群还共同拥有另外的隐藏属性。就像在测量时消失的负号一样,你无法直接测量这些隐藏属性,但它们会改变这些粒子的行为方式。
当你对调两个仲粒子时,这些隐藏属性会同步改变。打个比方,把这些属性想象为颜色。从一个内部是红色、另一个内部是蓝色的两个仲粒子开始。当它们调换位置时,它们并不保留原有的颜色,而是都以特定模型的数学规则所规定的方式相应地改变颜色。或许这种对调让它们分别变成了绿色和黄色。这很快变成一种复杂游戏,仲粒子在四处移动的过程中以看不见的方式互相影响。
与此同时,米勒也在忙于重新思考DHR定理。他说:“这些定理的含义并不总是十分透明,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数学构架。”
他的团队采用一种新方法研究仲粒子。研究者考虑了量子系统可以同时处于多种可能状态,即所谓的叠加态。他们想象对处于这些叠加态中的观察者视角进行切换——每个观察者对自身所处的实际分支的描述都略有不同。他们推断,如果两个粒子真的不可区分,那么无论调换的是处于叠加态哪一个分支的粒子,其结果都不会产生变化。
米勒说:“如果粒子距离很近,或许我会对它们进行调换,但如果它们相距遥远,我会什么都不做。如果它们处于包含二者的叠加态,那么我会在其中一个分支进行调换,而在另外的分支按兵不动。”不同分支的观察者是否以相同的方式标记这两个粒子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这种关于叠加态语境下的不可区分性的更严格定义将对可能存在的粒子类型施加新的限制。研究人员发现,如果这些假设成立,仲粒子将不可能存在。如果某种粒子真的能够像物理学家预期中的基本粒子那样无法通过测量加以区分,那么它们只能是玻色子或费米子。
尽管王志远和哈泽德先发表了论文,但他们似乎预见到了米勒即将提出的约束条件。他们能够证明仲粒子可能存在,是因为他们的模型否定了米勒的初始假设:就量子叠加态语境中所要求的完整意义而言,这些粒子并不具备真正的不可区分性。这将带来某种后果:尽管对调两个仲粒子不会对一个观察者的测量产生影响,但两个观察者通过相互共享各自的数据可以判断仲粒子是否被调换了。这是因为调换仲粒子可能影响两人测量结果的彼此相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区分这两个仲粒子。
这意味着有可能存在新的物质状态。在玻色子可以把无穷数目的粒子挤压到相同状态,而费米子则完全无法共有一种状态的情况下,仲粒子则介于二者之间——它们能够把少数粒子挤压进相同状态,直到发生拥挤并迫使其他粒子进入新的状态。究竟多少个粒子可以挤压在一起则取决于仲粒子的详细参数,即允许存在无限可能性的理论框架。
米勒说:“我认为他们的论文非常出色,里面绝对没有任何内容与我们的研究相矛盾。”
现实之路
如果仲粒子存在,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是被称为“准粒子”的演生粒子。它们表现为某些量子材料中的高能振动。
未参与此项研究的耶鲁大学物理学家程蒙(音)说:“我们也许能得到关于奇异物态的新模型,这些模型过去难以理解,但现在借助仲粒子可以轻松地得到解决。”
时常与哈泽德合作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实验物理学家布赖斯·加德韦乐观地认为,未来几年将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仲粒子。这些实验将用到“里德伯原子”,即电子与原子核极度远离的高能态原子。这种正负电荷的分离使“里德伯原子”对电场尤其敏感。相互作用的“里德伯原子”可以用来构建量子计算机,它们还是制取仲粒子的理想材料。
关于仲粒子的制取实验,加德韦说:“对于某种类型的里德伯量子模拟器而言,这差不多就是它们天生该做的事情。你只需让设备准备就绪,然后观察它们的演化就可以了。”
但就目前而言,第三类粒子仍完全停留在理论层面。
诺贝尔奖得主、提出任意子理论的物理学家维尔切克说:“仲粒子也许会变得十分重要。但目前它们基本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猎奇!”(编译/曹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