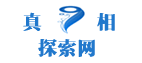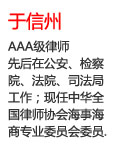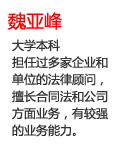民法中“人的形象”取自经济社会实践,亦因应实践的变迁而不断更始。现代社会人际交往的复杂化形塑了民法上诸多“人”的形象,或可说,现代社会民法中的“人”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以迥异的面貌示人穿梭于民法的古堡之中。揆诸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进化的旅程,不难发现,民法中“人的形象”变迁是法典理念与制度设计更化的根本动因。民法的理念转捩、范式转移以及价值递嬗无不根植于对“人”认识的深化。古罗马法学家尝言:“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人而制定。”《慎子》有云:“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准此可知,法因人而立,亦随人而变,法律上对“人”的认知不仅是制度生发的渊薮,而且是制度衍进的动力,古今中西,概莫能外。诚如日本法儒星野英一在其名著《私法中的人》中预言,“现代民法乃至民法学今后必须在‘人的再发现或复归’的理念下继续探索”,方能参透私法中“人”之真谛。但是,人的复归图景究竟为何,以何种方式完成人的再发现,星野氏并未给出答案。王雷教授新著《民法典中的人》从反思以财产为中心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出发,深掘中国民法关于“人”的具体创制,开创性的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统合21世纪民法中“人的形象”,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尝试。
一、缘起:现代社会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贫困
在十八世纪自然法与理性主义哲学的滋养下,民法上的人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颠覆性变革,锻造了在理性与意识上强而智的人像。上溯初民社会,延及古罗马,迄至中世纪的欧洲,人总是被打上身份的烙印。法彦有云:“体面的人,是一个有财产的人。”生活中的个体如果没有身份,则无法拥有任何财产,亦非法律上完全的“人”。法律上“人”的资格在古罗马专属于有公民权的家父,在中世纪欧洲则被封建庄园主所独享有。启蒙时代,通过对神学体系与传统权威的深刻质疑,贤哲们发现神学体系不足恃,传统权威不足法。人的主体性哲学将认识的基点从上帝转介到人本身,以内在的理性权威置换传统的外在权威。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标志性文件如英国《大宪章》、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人不仅是独立坚强、自力更生的,而且是具有改天换地能力的英雄形象。自此,个体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身份而获得其存在尊严,并且人作为自由理性存在的本质,可以通过意志自治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贯彻私人自治使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要形成者,民法以商人与市民为原型摆脱个体身份特征,打造了精于算计、形式理性、抽象中立并“在理智、意识方面强而智的人像”。此种以市民社会交易关系为范式旨在为财产交易实现所构筑的人像即观念上的理性经济人。
但是,民法上的人像在历经一个世纪的成长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社会实践的深化,被冲击的面目全非。立基于理性主义的“人的形象”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中反抗身份制社会的一面旗帜,对于从“身份到契约”社会进步运动的完成,功不可没。但是,国家强制的回暖与结构性失衡普遍化的现代社会,抽象平等、强而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过是一个浪漫的幻想。一方面,交易能力结构性失衡的普遍化催生了民法中“强而智”者与“弱且愚”者的主体分化。个体由于经济地位、信息资源等的落差,磋商对等性障碍成为常态,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不同类型的商人之间尤为明显。与其将“强而智”的面具强行戴到个体身上以削足适履的方式让交易实践适应人像假设,毋宁承认“弱且愚”者才是民法上人的主导面向。另一方面,面对理性经济人形象的坍塌以及由此诱发的私人自治走偏,国家再也不能以守夜人自居,而是积极介入市民生活,国家强制在民法中无处不在。理性人成为近代民法的基础与目的之后,个体成为法律关系主要形成者,但是国家从来不是旁观者,始终监管着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全部生命历程。现代社会交易关系中结构性落差普遍化后,理性人的抽象平等不复存在,民法形式逻辑的法律理性开始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公共政策、实质公平、实质自由、人本主义等观念的复兴。凡此种种,皆重塑了人的形象。
综上可知,现代社会的个体在奉行形式逻辑法律理性的民法眼中是孟德斯鸠所谓的“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在国家强制回暖、结构性失衡的时代甚至沦为强权阴影下弱而愚的一粒尘埃。这也是促使本书作者探讨民法上全新人像的深层关切与逻辑起点。
二、衍进:从抽象假定的人到具体真实的人
近代民法所假定的无色无味、不笑不愠之理性经济人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芳踪,社会特殊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不断扩编,终至具体人格的登场。民法上的人像亦顺势从“抽象假定的人”进化到“具体真实的人”阶段。面对传统人像假定概念失灵的窘境,民法社群尝试双管齐下实现对理性经济人的纠偏。
其一,在民法中迎回国家管制的传统权威,制定和强化具有限制性作用的框架。立法者、司法者通过打造各种监管工具以审查法律行为是否遵守了国家负责保护的基本价值。其实,现代民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曾经处于意思自治阴影之下的显失公平规范、公共政策等挹注实质伦理价值的国家强制工具不断侵蚀着立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私法规范机制。立法者在此种理念的指引下,因应缔约方身份的特殊性制定有别于普通私法的强制性规则,最终衍进出自成一体的独立规范体系,劳动合同法自立门户即为著例。
其二,恢复平衡谈判的条件以重铸理性经济人假设得以有效运作的环境。一方面,近代民法所假定的大多数“强而智”者随着经济社会实践变迁沦为“弱且愚”者,因应身份特征的倾斜性制度安排成为立法者的首选项。立法者为根治当事人之间的结构性失衡,鼓励弱势方组成团体从而形成与强势方平起平坐的磋商能力,如个体通过工会、协会等身份补强扳手腕实力即为成功范例。另一方面,鉴于信息失衡是现代民法上人们强弱、智愚之分的渊薮,立法者强制信息优势方披露有关交易的重要信息,抹平信息落差诱发的磋商能力鸿沟,从而确保弱势方得以在信息平等的基础上完全自主的做出决策。由此可知,现代民法上围绕实践中具体而真实的人之特点尝试做出针对性补强,以实现强弱双方武器上的平等。从外观来看,现代民法上对人的认知颇有些许因人立制复归到罗马法上以家庭、公民等集合概念而非独立个体标识“人”的意蕴。
诚如本书作者指出:“这当然不是向身份制的复归,而是推进对社会特殊群体苦难的关照。”换言之,此种从契约到身份的“复归”是通过身份的加持使得弱而愚的个体匹配强而智的假设,辅之以运行环境的纠偏,从而捍卫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专门针对民法上“人像”的现代调试。准此而论,本书认为现代民法的经典人像系社会特殊群体似乎并不准确,更精确地说法或许是,现代民法上的人是披着特殊身份外衣的理性经济人。
由是以观,现代民法上所谓具体人格的登场并非对抽象人格的否定,而是比照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运作条件对现代社会具体而真实的人进行针对性扶持,以期将具体人格回复到抽象人格的样态,进而,维持近代民法诸多制度赖以运行的体系。可以不讳地说,现代民法对具体且真实人的关注、倾斜性保护并未跳出近代民法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窠臼,毋宁说是因应经济社会实践变迁进行了小修小补。
三、革新:社会主义民法中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鉴于近现代民法面对“人的形象”与“交易实践”之间脱节应对乏力,本书深掘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人法品格,尝试还原民法中完整且真实的人之全貌。
首先,从财产中心主义转向以人本主义,完成民法上人像构筑基点的更迭。自由放任时代,为贯彻私人自治以商人与市民为原型所打造的人像,其社会关系范式系财产交易,具体的制度配置亦是围绕人们之间的财产展开。近代民法实质化转向后,对劳动者、消费者等领域特殊群体的关照,旨在恢复人们之间的武器平等,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基石仍未动摇。其内在理念仍然是回到抽象平等的样态。因此,近现代民法人像构筑的基点均取向财产中心主义。本书则反思重物轻人的民法传统,主张21世纪应当重新发现人的价值,以基于人本主义理念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取代立基于个人主义理念以财产为转轴打造的“理性经济人”。本书在第四章发掘民法对生命尊严的关照、第五章对民法初心的剖析均笃力找回民法上人像被理性经济人假设所遮蔽的实质伦理内涵,彰显民法人文关怀的精义。本书第二章对民法上特殊群体关爱义理的阐释、第三章还原民事交往实践中具体人像亦折射出财产法的伦理意涵。当民法上人像被个人主义方法论所剥离的伦理性再次“复归”,财产法的各项制度的解释与适用也将带来颠覆性的变革。作者基于民法人文关怀与自由之精神兼备的理念革新了民法上人像构筑的基点,开示其以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统合财产法与身份法的理论雄心。
其次,从理性人到完整的人,彻底冲破个人主义方法论给民法人像套上的枷锁。近现代民法所立基的理性经济人是完全自由、完全认知、完全平等,其人像构筑的终极目标是打造财产法上的适格主体。民法以规制财产交易为本旨,个体是财产的孤独守护者,国家是财产的守夜人。作为新世纪典范的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其功能从单纯交易规制法进阶到治国理政的重器。国家不再停留在消极自由意义上的守夜人角色,而是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市民生活,为积极自由的实现创造空间,也即作者主张的“民法的任务就是纾解人们的懊恼与愁苦,增进人们的欢喜与快乐”。本书敏锐的捕捉到了法典功能进化与国家角色转型背后民法上人的主体性与精神价值的重光,并跳出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窠臼致力于探究民法上完整的、活生生的具体人像。作者承认他们认知的非至上性、非形式性以及意志自由的限制性,并以此为基础为我国民法上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绘像。从这个意义上讲,王雷教授系汉语法学界首次生动刻画了21世纪社会主义典范民法典的群体人像。
诚然,本书作者尝试打破财产中心主义的人像设定,意图以全新的民法人像统合身份法与财产法的理论雄心,令人钦崇。但是,本书对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之内涵与特征的阐释似乎并没有理性经济人那么清晰,直接导致在理性经济人之外补缀伦理人、情谊人、团体人、生态人的人像类型亦无法精准界定,具体统合的抓手亦有待深究。
其一,本书在“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统合下以全新身份样态补绘理性经济人形象之时,缺乏精致化的类型理论,其逻辑周延性不无商榷余地。作者敏锐的察觉到现代民法对人像的小修小补并不能涵摄二十一世纪民法中人的全貌,并提出我国民法中承载不同价值维度的伦理人、情谊人、团体人、生态人四类全新的身份形态。与现代民法通过“身份”使具体的人复归理性经济人不同,本书似有反其道而行之的意蕴,尝试将理性经济人降格为一种“身份”,与其他四类身份并列来标表民法中的全部人像,并将之统摄在“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之下。遗憾的是,作者并未将经济理性人、伦理人、情谊人、团体人、生态人在逻辑上实现精准的区分,或者这五类人根本无法截然区分。经济理性人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承载着独特的历史使命与实践价值,但是伦理人、情谊人、团体人、生态人等在具体交易中可能是理性经济人,也可能是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似乎不具有独立的规范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更似因应经社实践发展扩容现代民法特殊群体的类型,枚举交易模式创新所产生的个体身份创新。或者对弱而愚者的具体分类进行了精细化挑选,似乎尚未完成民法上人像质的跃升。此种开放性外延,是否意味着科技进步与实践发展会生产更多特殊群体与“人像”类型,他们是否可以直接嵌入目前民法上“人”的群像之中?因为只有构建了关于人的一般化理论,才能保持法典对经济社会实践发展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否则,各类具体的人将如特鲁伊木马一般不断涌入民法,但是却找不到自己的坐标。而且缺乏一般抽象化理念作为支撑的经典人像,将使得民法上人的发现极有可能仍然停留在“原则(理性人)-例外(特殊群体)”的框架下打转,也即原则上是理性人,例外才保护日益繁多的特殊弱势群体,未能真正跳脱于理性人假设的窠臼。
其二,通过经典人像实现对财产法与身份法的统合,仍需要进一步寻找适切的制度抓手。本书在反思传统财产中心主义经典人像构筑的基础上,提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作为21世纪民法统合财产与身份两大体系的经典人像。为贯彻私人自治,近现代民法将意思合致作为法律行为效力的唯一根源。以财产交易为市民社会关系模型将伦理从民法中剥离出来,以致传统观点认为伦理性为身份法所独享。准此而言,意欲统合财产法与身份法比较适切的路径或许是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将伦理性挹注回理性经济人以及财产法规整体系之中,交易不再是力量的表征,而是一种真诚合作的工具与相互信任的事业,法典的功能转向与制度重释也在此统合基础上找到了支撑。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所刻画的经典人像诸如理性经济人、伦理人、情谊人、团体人、生态人与其说是作者所发掘各具身份的人像类型,毋宁说是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具有经济理性、伦理性、情谊性、团体性、生态性的多元面向。由此可知,通过回填实质伦理内涵到财产法之中,不仅实现了财产法与身份法的真正统合,而且在完整且真实的人像要素基础上,找到了民法上不同身份群像的统合路径,从而完成经典人像的重构。
四、结语:民法中“人的形象”探讨永远在路上
近代民法的人像助力社会运动从身份到契约的嬗变,现代民法的人像则通过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向进路企图将具体真实的个体重披理性经济人外衣,我国民法上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像是回归身份,还是走向契约,抑或有第三条道路?破费思量。本书深刻反思财产中心主义的民法人像构筑原理,提出人本主义的全面自由发展人像理论,将身份法从财产法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同时为现代社会实质伦理内容回填财产法构造了主体性基础。以全新的人像为起点,作者笃力打造一种最佳的民法上私人自治境界,民事活动中意志自由固不可废,但公平与合作的增进需要尤为关注。打造伟大法典,成就伟大法学,一直是民法社群的共同期许,重新发现民法上的完整人像无疑是起手式,或可说,21世纪民法以及民法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作者提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像基础上,因应实践不断补绘经典人像的要素,进而探究民法基本原理与制度的重释方案。
(文章主体内容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6日刊发)
备注:“本文已征得作者授权,主体部分刊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参见https://epaper.csstoday.cn/epaper/read.do?m=i&iid=6951&eid=50121&sid=232131&idate=12_2024-11-06_A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