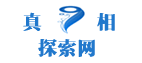张树森老人出生于1936年,是河北省定兴县肖村营一户普通农民的儿子。命运阴差阳错之下让他在青年时代来到上海,他在这里作为一名纺织人为新中国的建设挥洒热血,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张树森今年虚岁九十了,他见证了纺织业在上海的发展和腾飞,也经历过改革的阵痛。他做过市劳模,他的参与设计的作品曾出现在化学词典里。有过一些未酬的志向,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
属于张树森这辈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们在那个时代里曾经认真、踏实地活过,这样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他将自己一生中的照片、证书、书本、字画等旧物逐年收藏起来,如今已堆满了家中各个角落。对于他存在过的痕迹和活出过的价值,它们是最好的证明。
但张树森已步入了生命的暮年,有一天当他离开后,他的一生所藏还有什么意义?谁还会去费心打听他的故事?念及于此,他的外孙Leo和自己的俄罗斯未婚妻飒纱决定用他们的方式“抢救”外公的珍贵档案和物件。
在Leo的提议下,两人拍摄制作了系列短片《我的中国外公》,用短视频的方式讲述外公的故事,用画面留存外公的收藏,并在国内外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渐渐的,外公的故事也火到了外网。
一段时间以来,这对年轻人意识到,他们做这件事情产生的实际意义已经远超自己的预期。原本只是想保留一段外公的私人记忆,但却在无形中影响了其他人。外公的视频激起了中外网友对于自己家族史的探究兴趣,也启发他们重新审视自己和祖辈父辈间的关系。
我和中国外公
我们都是外来者
某种程度上,飒纱认为自己和外公的人生轨迹是相似的。“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他当年从河北来到上海,而我则是从俄罗斯来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让她对张树森在这座城市的打拼经历产生共鸣。
因为她了解一名外来者的心态。听外公分享自己上世纪50年代初来乍到时的种种,她会忍不住回忆起自己来上海攻读研究生时的心情,回忆起那种跃跃欲试里带着一些谨慎的心态,担心行差踏错,也不确定能否融入城市的文化中去。
张树森来到上海,是命运的使然。1954年夏,初中毕业的他面临着一次升学的选择。

张树森的初中毕业证书
他同时填报了石家庄纺织工业学校和北京财经学校,在当时,北京是全国进步青年的梦想之地,对于张树森也不例外。
但那个年代车马慢、邮件也慢,路上可能状况百出。他先收到了来自石家庄的录取通知书,直到已经去纺织工业学校报到,北京财经学校的通知书才姗姗来迟,晚了整整一个月。“如果先拿到的是北京的通知书,我后来的人生就不是今天这个样了。”外公总是这样对他们说。

迟到的北京财经学校录取通知书
那张迟到的通知书,被他保存至今。早已泛黄的纸张,承载了一段飘渺的记忆。“……以上各项务希切实注意,按时办理,不要延误。附注:报到时随交户口迁移证。”纸上每个字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从拿到手上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若干年后,包括张树森在内的10名纺织工业学校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上海工作,他和另外两名同学进了纺织工业局下的仁丰染织厂,后来改为上海手帕一厂。
“外公的人生中有很多转折点,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段。如果不是因为这封信最终晚了一个月才送到他家里,那么后来他整个人生的走向都将彻底不同。”飒纱感叹,“往深了想,这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命运。一些看起来这么小的小事,却往往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你的人生。”
“他当时很可能对于自己没去成首都而感到失望,但是人生这个偏差数年后最终促成他来上海,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妻子,组建了家庭,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在上海的工作。外公所经历的再一次向我们证明,每件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飒纱有时候想,自己来到上海也是冥冥中早就注定的事情。她从小对于亚洲文化感兴趣,为此前往韩国留学。在韩国读完大学,又来到上海继续读研读博。

飒纱目前正在上海读博
“我第一次来上海旅游是2019年三月,我第一眼就爱上了这里。因此当时就决定,我要在中国继续自己的学业。”还在俄罗斯时,她就已经开始学习亚洲文化。
“一直以来,我就深深被亚洲的文化吸引。不巧的是,当我在韩国学习的时候,我没能在那里找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寻找的东西。但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要找的就在这里。这些年,人们不停地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国家,我说,100%是中国。” 保存至今的入党申请书
“不愿做一个一辈子庸庸碌碌的人”
上世纪50年代,当年轻的张树森来到上海时,他也深信会在这里找到自己内心长久渴望的一些东西。
半个多世纪后,80岁的他写了一本回忆录,在回忆最初的那段时光时写道:
“百年来,充满活力的上海人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求新求变,推动这个城市的发展,赢得了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尤其是上海的纺织业,几乎占上海工业、占全国纺织业的半壁江山。能从事这个专业,我感到无比自豪,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在呐喊:要加倍努力,争取当一个称职的工程师,让自己的梦想在这个城市腾飞。”
俄罗斯人飒纱在2019年所看到的上海,早已不是张树森在60多年前看到的那个上海,但这座城市的精神向来是一脉贯通的:上海不讲究一个人来自哪里,重要的是他知道想去哪里,并以自己的方式奋斗拼搏,最终抵达目标。
1959年4月,张树森被发展成预备党员,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底稿被他完好保存到今天。飒纱对其中的一句话记得很牢,“我要使我的一生生活得有意义,我不愿做一个现状维持派,亦不愿做一个一辈子庸庸碌碌,又不长脑袋的人……”

张树森的入党志愿书
这句话让她想到了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张树森很高兴,他说写这封入党申请书正是在自己受这本书影响最深的那段时间。
当时,中国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棉花欠收,原材料严重缺乏,纺织业开工不足,仁丰染织厂已无布可染。听说上海光中印染厂正在进行化纤攻关,且已有了一台可以生产的“五合机”(注:用传统方法生产粘胶液,要经过碱化、粉碎、老成、磺化、溶解五道工序,在不同设备中完成,而在“五合机”一部机器内便可完成这五道工序)正在安装,张树森便被派去学习业务。
有了“五合机”,就可以生产化学纤维,而不必再依赖棉花进行织造。

张树森向我们展示自己画的“五合机”草图
完成学习的张树森,带着自己画出的“五合机”草图等资料回厂。大家立刻按照他画的草图进行制作,有的部件通过外加工,两个多月就搞出一台仿造的“五合机”。
“九月底开始试投产:第一次投料连续苦战29个小时,于10月1日凌晨5时,纺出了第一束丝向国庆献礼。”
在当时的中国,化学纤维是新生事物,懂行的人不多。因此1962年,上海纺织设计院请张树森去该院,希望他对新型“五合机”提供初步设计资料。他花了一周时间出了机器草图,并提出工艺参数。
后来采用他提出的技术数据,由上海机电设计院进行详细设计后推广到其它工厂使用,在纺织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化学纤维词典》中,对这种“五合机”还作了专门介绍。
人生就是这样
总会碰到不由自己控制的无奈
由于在化纤技术攻关方面作出的成绩,张树森于1963年被评为1960年-1962年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他的照片也被放在长阳路上的画廊橱窗里进行展示。

当年在长阳路上展示的照片
当年和他同一批获得市劳模的人里,有一个成为了他此后的人生伴侣。1968年1月10日,张树森和山东姑娘刘同英结婚。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恰逢提倡破四旧,因此婚事简办。结婚那天,俩人相约公共汽车站碰头,然后一起去海宁路四川北路口一家饭店的楼上“叫了几个菜,吃了一顿饭了事。”他们没有拜过堂,也没拍过结婚照,“糊里糊涂算结了婚。”

外公外婆结婚时借住的老房子
“一时间没有婚房,厂里一名热心女工腾出自家楼下一间不到12平方米的吃饭间给我们做了新房,地址就在杨浦区茭白园路154弄205号。没有煤气也没有卫生设备,主人说不收房租,让我们住半年解决临时困状。”他回忆,
“我们将墙用石灰水刷了一遍,屋顶糊上纸就是新房了。家俱就是一张床,一个小方桌,四把椅子,一个五斗橱。虽然贫寒,却也充满着家的温馨。”
张树森给飒纱看当年“婚房”的老照片,透过照片,外公外婆60年前的生活在飒纱眼前渐渐铺展开来。俄罗斯姑娘想象着两人在动荡年月里如何相互扶持支撑着度过,想象这对原本充满了远大美好志向的年轻夫妇,在经历了幻灭后,如何彼此打气,成为另一半唯一的慰藉……
这种想象的经验对于她而言是陌生的,但她终于渐渐懂得,这就是老一辈中国人的爱情,不离不弃胜过任何甜言蜜语。

外公外婆结婚20多年后补拍的结婚照
人生终归会柳暗花明,那十年过去后,张树森重又成为单位骨干。1984年,他和业内几名同行前往联邦德国考察。那张标注了“沪府办外(1984)930号”的批件也被他悉心留存,通过这份批件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公派出国还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直接发文的。

市政府办公厅批文
在德国,张树森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可口可乐和矿泉水。因为舍不得丢弃,便将空瓶攒起来背回了国。考察期间每天有补贴,他省下补贴,回国后在当时的特供商店买了一台18寸的飞利浦彩电。

出国考察期间留影
“改革开放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多元开放,国家和个人免不了都在探索中冲突、在冲突中成长。”张树森所在的纺织业经历了几次改革,1987年,“上海市纺织科技发展中心”成立,他被调任开发部主任。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纺织工业局的体制也开始发生进一步变化。”
1995年5月24日下午,在上海纺织机构改革大会上,时任市委组织部部长的罗士谦正式宣布撤销纺织局建制,新建“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记录纺织工业局从外滩24号撤牌的这一天:
“想当年,它是上海最大的工业局,被称之为‘母亲工业’,旗下有400多个下属单位,50多万职工,气势何等宏伟。可如今却要销声匿迹了,谁心中都有太多的不舍,有道不尽的牵挂,有的甚至悄悄流泪。人生就是这样,总会碰到许多不由自己控制的无奈。几十年的旧体制被打破了,在新旧体制的摩擦、撞击中,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次次的阵痛。”
1997年,张树森光荣退休。
如果你愿意停下脚步
花时间与祖辈、父母相处……
退休后的张树森,拾起了早年便爱好的书法。飒纱每次来看望外公外婆,最喜欢往两人的书房跑。两个老人在这个房间里度过了最长的时间,外婆画画,外公练字。
“中国书法有一种特殊的美,因为每个字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样。”飒纱鼻翼翕动,嗅着空气里的墨汁气味,“尽管我还看不懂他写了什么,但Leo会翻译给我听,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用毛笔写字,并且达到他的1%。”

画是外婆画的,字是外公写的
“外公很早就开始练习书法,但当时他的工作占据了太多时间,因此直到退休后才有时间好好投入其中,认真钻研起这门艺术。”飒纱说,“这其实很能展现中国人的一种特质:人们日复一日辛勤工作,将毕生精力投入事业。他们的目标如此坚定,不会轻易被其他事情分心。”
“而外公身上最让我感佩的一点就是他的用心钻研,无论是当时研究‘五合机’,还是退休后练习书法,他的这一特质是始终如一的。即便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但他依然修炼到了大师级别。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他的作品屡屡获奖、展出……”

飒纱觉得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的生命
听外公讲的故事越多,飒纱越明白了未婚夫Leo曾经对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你可以从书中了解很多知识,但它们和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始终是不一样的。”她感到庆幸,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
让Leo感慨的是,关于外公的很多事都是自己之前不知道的。他也是在拍摄这一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老人的往昔。
年轻人的生命里好像永远按着一个快进键,他此前好像从未停下过脚步,耐心听家中的老人讲讲过去的故事。“外公外婆住在松江,和我们离得比较远。因为要拍这个短片,来得勤了,交流得更多了,就感觉我们爷孙之间的情谊连结得更紧密了。”

Leo在拍摄短片的过程中渐渐了解了外公的往昔
他和飒纱打算等他们将来一起回俄罗斯的时候,也要为飒纱的祖辈拍摄制作同样主题的系列短片。青年人对于自己的长辈似乎总是兴趣寥寥,但有一天当他们也来到生命的中段,想找寻自己人生的来龙去脉,才发现可以讲述家族历史的人都已经故去了。这样的遗憾,无疑是巨大的。
“人们年轻的时候,往往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飒纱说,“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会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应该向老一辈学习讨教的地方。但许多时候,机会已然流逝——那些承载着传统的一代人已渐渐离去。这种错位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身边的一切都那么新鲜,大家渴望探索更多、学习更多。他们和老年人的生活节奏存在巨大差异,老一辈习惯于慢节奏地品味生活,而年轻人则沉醉于快节奏的蓬勃活力之中。”
“俄罗斯文学里有一部经典作品,是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这部小说讨论的,正是关于不同代际间的鸿沟。这种代际间的疏于沟通,本质上是一种悲剧。但你知道吗?如果你愿意停下脚步,花时间与祖辈、父母相处,一定能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他们的人生中曾经历过的,可以教会我们的。”

《我的中国外公》短视频系列已经发布了很多期
飒纱想起在他们录制视频过程中发生的一件小事,当时外公正在镜头里回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接起电话后只说了两句,她和Leo就都明白了这只是一通再明显不过的诈骗电话。
但是外公却展现出了巨大的耐心和礼貌,仿佛电话的那头是个寻常的老友。也许,他只是太渴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了。这一刻她意识到,老年人的孤独或许超出了自己之前的想象。
她和Leo约定,日后即使在不拍摄的日子里,他们也要常来看望外公外婆。
后记
《我的中国外公》系列视频不仅在中国的社交平台发布,在借助科技手段自动添加了多国语言的字幕后,还可以同步上传到国外的社交媒体。
“对于我们和外公而言,最珍贵的收获莫过于看到更多人开始探索自己家族的传承,没想到视频的影响甚至跨越了国界。”飒纱说,“这证明了,我们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
到了人生中的某个阶段,一个人自然而然会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产生回溯和挖掘的兴趣,这恐是人之常情。
1963年,回乡探亲的张树森让自己的父亲口述了他的个人史,后来将这份口述整理成文字,记录了下来。

张树森父亲的口述史
60年后,当他将自己保存的这份口述史展示给飒纱他们看的时候,外孙Leo在那一刻突然被一种莫名的情绪击中了。
“就像我们会好奇外公的历史,外公也会对他前人的历史感兴趣。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其实为外公家族的历史生成了一个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