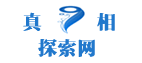她叫特拉斯,曾是英国首相,如今美国《政客》杂志在文章中形容她为特朗普的“迷妹”。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媒体《政客》的报道,曾创下首相任期最短纪录(49天)的英国前首相特拉斯,近日在印度媒体《印度斯坦时报》举办的一场国际论坛上公开表示,她认为英国也需要一位像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一样的领导者。

图为外媒报道截图
据《政客》网站介绍,特拉斯一直认为她本可以给英国经济带来复苏的政策,但在英国的官僚机构里遭遇了层层阻碍,尤其是英国的财政部和央行。
“从那之后,她就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政客》网站的文章写道,“她还参加了今年早些时候(在美国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在期间呼吁共和党去对抗‘深层政府’”。特拉斯还曾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公开展示过自己参加这两场活动的照片。
此次在印度发表讲话时,特拉斯称特朗普在美国掀起的“革命”或将在未来5到10年里席卷欧洲,因为欧洲也充斥着美国人那样的不满。不过,特拉斯并不认为自己是她口中那个“英国的特朗普”。
“我已经染指过那团火焰,然后被严重烧伤了”,她说。
延伸阅读
看到卢比奥时,欧洲外交界还在美,然后就笑不出了
文 观察者网 杨蓉
即将二次入主白宫的特朗普陆续公布了其颇具争议的内阁名单,引发欧洲盟友不安。“政客”新闻网欧洲版14日披露,在特朗普选择“对华鹰派”、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出任国务卿时,欧洲外交界尚且保持“谨慎乐观”,但很快就因后续其他并非持传统“亲欧挺乌”立场的人选而陷入恐慌。

特朗普提名马克·卢比奥为美国的新一任国务卿人选
报道称,本周初,当卢比奥作为特朗普国务卿人选的名字首次出现时,欧洲外交官甚至对美国新内阁的阵容感到“些许宽慰”。在欧洲、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官、专家和官员看来,卢比奥在外交政策上经验丰富,且支持北约,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态度强硬,是“适合特朗普”的人选。
紧接着被提名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沃尔兹,也被认为是个“安全的选择”。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和沃尔兹可能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但最终还将维持华盛顿先前对乌克兰和台湾的所谓“防务承诺”。
按照外交政策分析家乌尔里希·斯派克(Ulrich Speck)的说法,欧洲政界最初的反应是“如释重负”。报道说,和许多欧洲政界人士一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外交官表示:“他们没有其他人那么可怕。”
然而,“好景不长”,特朗普提名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加巴德出任国家情报总监、福克斯新闻电视主持人海格塞斯出任国防部长后,“政客”新闻网欧洲版称,人们变得更为担忧。
尤其是加巴德,她曾会见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拥抱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2月俄乌刚刚爆发后三天,她还曾呼吁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领导人“拥抱Aloha精神”(源于夏威夷语,指和谐共处),就乌克兰成为中立国达成一致。这些都被西方官员看作踩了欧洲安全的“红线”。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27日,加巴德出席共和党竞选集会
前法国欧洲事务部长、欧洲议会复兴欧洲党团议员纳塔莉·卢瓦索(Nathalie Loiseau)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这真的很可怕。”欧洲议会安全与防务小组委员会主席玛丽-阿涅斯·施特拉克-齐默尔曼(Marie-Agnes Strack-Zimmermann)则悲观写道:“欧洲保持克制并希望美国保护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波兰前驻美国大使马雷克·马杰罗夫斯基(Marek Magierowski)对加巴德过去的“亲俄”言论颇有微词。他做客波兰电视台节目时说:“当她成为整个美国情报界的首脑时,这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信号。”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欧洲高级顾问弗朗索瓦·埃斯堡(François Heisbourg)称:“这是个严重的大问题,而且很糟糕。”她在X上写道:“我希望(美国国会)参议院能阻止她的任命被确认——但我不指望这会发生。”
一名欧盟外交官表示,考虑到特朗普推行“推土机式”外交政策的风险,欧盟必须做好准备,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即使这两位先生(卢比奥和沃尔兹)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更温和的态度,也不能免除欧盟准备做更多工作的责任。”
在欧洲外交界看来,更大的问题是,上述提名表明,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他的内阁“不会有任何制衡力量”,因为被提名者的政治生涯或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朗普的支持。
欧盟官员和外交官指出,特朗普过去就倾向于越过内阁官员,甚至美国情报机构,直接与外国领导人进行谈判,其第二任期可能更为“专断”。一名欧洲外交官说:“我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可能根据幕僚人选对本届政府的走向做出任何明智的预测。”
报道提到,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里,曾担任两年防长的吉姆·马蒂斯,一度被视为特朗普的克制力量或“房间里的成年”,但在与特朗普总是意见相左后被解职。特朗普任内“炒掉”的第三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10月警告,特朗普2.0时期的外交政策立场可能会比1.0时期更激进,“他退出北约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跨大西洋关系中,我们将面临非常、非常艰难的几年。”埃斯堡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