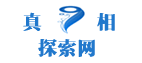就中国历史上的读书人而言,庄子永远是他们精神追求上遥不可及的巅峰。这种巅峰的文化意义,在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进入“坐忘”境界的庄子,是世俗完全摆脱、心灵彻底自由的一个象征。所以,庄子作为“图腾”,始终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仰慕,所效仿。在他们看来,庄子那种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学(“不傲睨万物,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乃是“十有九人堪白眼”处境中的自己最好的精神慰藉。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动朝着这方面做努力,如“浑身上下静穆”的陶渊明;有的人则是在人生道路上摔了跟头之后再回过头来寻觅庄子这个精神港湾,如李太白、苏东坡。不过,殊途而同归,这恐怕也是事实。
其实,庄子是人不是神,他的德行、他的修为也并非一朝一夕精进到这样的地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即便是天才,他离开娘肚子的第一声哭,也同平常的婴儿一样,而绝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诗或者是一曲动听的歌。依我看,庄子能够参悟天地的奥秘、省识人生的玄机,恐怕有幸依赖于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机。换句话讲,庄子与官场的种种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从而真正超越了世态常情的羁绊,走向了“一是非而齐生死”的境界。
众所周知,中国读书人的千般苦闷、万种烦恼,都出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社会世态。作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细毛,还是软毛硬毛、长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会体制这张“皮”上,而毛的意义、毛的作用,按传统的认知理念,则又在于能否当官,进入主流圈,拥有话语权,而不被边缘化。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云云,其实就是指读书人能把自己的知识、智慧、能力开出一个好价格,兜售给帝王家,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当然这只是在“吾皇圣明”的盛世时代),换取一顶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这样才算是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达则兼善天下”。于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地往仕途上挤,挤得龇牙咧嘴,碰得头破血流。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乐观其成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理想场面。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能标榜什么“精神自由”,奢谈什么“人格独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暂时当稳了奴才,有了“扯淡”、“帮闲”甚至于“帮忙”的机会,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趋,做得好一点的,争取当一个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则不免“为虎作伥”,祸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人与官场关系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的自然本色还能保持几许,他的心灵自由还能留存多少。庄子、陶渊明等人与官场瓜葛比较少,他们的精神自由空间便相对宽阔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懒觉,梦蝴蝶,“鼓盆而歌”;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可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王摩诘、李太白、苏东坡等人对于官帽比较热衷,老是幻想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角色,殷切期待着“天上掉馅饼”一类好事的发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因此,他们的心灵便难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寻烦恼,“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了。至于韩愈、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曾国藩之流,亦官亦学,一副“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的腔调,尽让人看了恶心,则更是自桧以下,不足具论了。庄子的走运,我觉得正在于他仕途上的坎坷,因此而避免了“失足”的尴尬,摆脱了“沉沦”的危险。不管是出于养家糊口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考虑,庄子他一开始也不怎么清高,不怎么潇洒,也曾涉足于仕途,在宋国蒙地当过一阵子“漆园吏”。
这个管理漆园的官职,至多相当于今天小小的科长,不入流,没有品,收入不会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责任不轻,辛苦多多。一年到头要为漆园的经营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脱皮,冬季在寒风之中冻得手脚裂口,既没有了读书抚琴的时间,又丧失了吟诗作画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当时属于国家战略物资,修缮宫殿需要它,制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它。所以国家对它的出产与质量加以关注和重视乃是势所必然,理有固宜。这意味着上级官员动辄要莅临漆园,考察监督生产的进度,考核审计工作的实绩。不过如此一来,庄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劳心费神、加班加点整理汇报材料,编造各种数据,填写各种报表;不得不低眉顺眼、哈腰迎往送来,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断经历从“豪言壮语”到“花言巧语”,止于“不言不语”(完全醉倒,钻到桌子底下,不能吭声的最高酗酒境界)的游戏过程。这种日子,就像《聊斋志异》“促织”篇中那位可怜的小吏成名那样过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如何让生性自由的庄子能够忍受。陶渊明好歹还是个县令,正儿八经的“正处级”,可他尚且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回乡下老家种瓜栽豆,过自食其力的生活,“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庄子他的“漆园吏”官衔比起县令来,又低了不知多少级,当然更不愿为“五升米”折腰了。于是乎他的选择也就只有一个:趁早辞官,去做“涸辙之鲋”,到烂泥沟里自由自在去摇曳自己的尾巴,“无己”、“无名”、“无功”、“无待”。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最初的动因,恐怕是嫌官职太小,只有办事的辛苦,没有吆五喝六的快乐。
不过,问题又来了?押庄子嫌漆园吏官小位卑,有苦劳没功劳,所以撂挑子不干,似乎说得通,可是当楚国国君千里迢迢派遣专使恭请庄子去当宰相,庄子还是不干,这又是什么道理?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职重而权大,应该是读书人所追求的最显赫、最荣耀的仕途顶点吧。可是庄子居然不识抬举,表示只做烂泥塘里翻跟斗的小乌龟,不做那庙堂里面供瞻仰的大乌龟,三言两语谢绝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让楚王的专使(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或人事局长)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简直是犯迷糊到了极点。实际上这样看庄子才是蠢,庄子本人可一点也不傻,倒是绝顶的聪明。在他看来,宰相这个官职太大太高了,就像《荀子·王霸》所称,宰相拥有“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的大权,一旦爬上这个位置,地位自然是高了,俸禄自然是多了,威风自然是有了,享受自然也是少不了了。有金银源源不断送上门,有美女纷至沓来偎上身,荣华富贵如春风似秋雨,挡也挡不住。可是常言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人出于众,毁必随之。”在拥有巨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更得处于巨大的危险。
在君主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还不是让老虎一口吃了!范睢当年身为宰相,够厉害了吧,还不是被秦昭王用几句话便打发他送了命。连白起这样的功臣宿将,邯郸一战打得不好,自己的小命便莫名其妙给赔了进去。礼聘庄子的楚国,情况更是糟糕,做宰相的,下场大多都不是太妙:春秋时,城濮之战失利败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断,让对手晋文公乐得心花怒放,连声叫好:“莫余毒也!莫余毒也!”战国时,吴起当宰相辅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国面貌大变,一跃而成为战国七雄中的龙头老大,可结果却让恩将仇报的楚国贵族大佬扣上“谋叛”的帽子,不由分说用乱箭射死。这说明官大有官大的难处,尤其是像宰相这样的特大号高官,完全不是聪明人该干的。庄子他学富五车,知古识今,自然懂得这层道理,哪里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禄开玩笑,当然不会接楚王送来的宰相委任状。由此可见,庄子不愿当官,有时又是因为嫌官职太大,虽有当官的神气、威风,但有更多当官的危机,作为明白人,这种致命的游戏唯恐避之不及,又怎么会掺和进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
小官不屑干,大官又不愿干,那么,庄子难道真的对当官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吗?我看其实也不见得。庄子成为大思想家后这方面的心态我不敢妄加揣度,但是其早年恐怕是不会彻底拒绝当官的诱惑的,否则,我们便不能解释他为何连漆园吏这样的芝麻官也一度做得。按我的看法,庄子内心真正想做的官是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这种中等官一方面无须去承担过重过大的责任,不必一天到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似的侍候身边的国君,以至于稍不留意,颈上的人头莫名其妙给搬了家;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权力,一定的威风,有下属可供驱使,有“小蜜”可供消遣,有油水可供打捞,没有太大的风险,不必像最基层小吏那样忙得头昏脑涨,手足胼胝。
庄子自己曾说过,做人要把捏分寸、恰到好处,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做官问题上的夫子之道:即做官也应该处于材与不材、不大不小之间。而历史也证明了庄子的远见: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苏东坡的《前赤壁赋》等永垂不朽的篇章,岂不都是在他们当太守、团练使这类中不溜儿官员时写成的吗!可见,对读书人来讲,当不大不小的中官,恐怕是“入世”与“出世”两不相误的较好途径,也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比较理想的选择。
在庄子身上,这种“材与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所以到后来他也就干脆完全杜绝了仕进的念头,“终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场与态度打发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谴是非而与世俗处”,在绝对自由的精神王国中驰骋自己的天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就中国历史而言,或许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个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视千古、伟大不朽的思想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