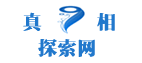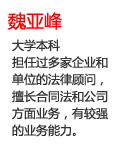一位老人在病床上发出异样的声音,守夜的护士艾伯塔连忙走来探视。老人喃喃地说着她无法听懂的语言。两声沉重的喘息后,他静静地去世了。后来人们推测,老人临死前说的是他的母语德语——七十六年前,他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乌尔姆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名字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哈维的等待
当夜,病理医师托马斯·哈维(Thomas Harvey)打开了爱因斯坦的头骨,往脑动脉中注入防腐剂,把大脑泡进固定药水,这颗前无古人的大脑被保存起来。虽然哈维医生许诺将爱因斯坦的大脑用于科学研究,并从爱因斯坦家人得到许可,这一举动还是引发了无穷争议。甚至有几位著名的神经病理学家强烈建议哈维放弃这些样品,可是哈维拒绝了。很快,他被普林斯顿医院解职。
随后的半生里,天才的大脑一直伴随着哈维,带给他厄运也带给他短暂的盛名。他经历了离婚、长途搬家、失业和吊销行医执照。他后来成为堪萨斯州的一名塑料厂 组装工人,与“垮掉的一代”中的著名颓废诗人威廉·伯罗斯(William Burroughs)为邻,两人经常称兄道弟,小酌痛饮……虽然伯罗斯曾常常吹嘘“我想什么时候搞到一块爱因斯坦的大脑都行!”哈维却对这些样品视若生命。1997年,哈维带着大脑样品与记者麦克·帕德尼提(Michael Paterniti)一起横穿美国去加州拜访爱因斯坦的孙女。他曾经计划把这些样品送给科学家的后人,但是他最后改变了主意,迅速地离开了她家。在帕德尼提的描写中,哈维是个怪异的老人,充满了唐吉诃德式的幻想,时时爆发出莫名其妙的大笑。
直到2005年,他才把样品交给普林斯顿医院。而此时,距离爱因斯坦的骨灰被撒在特拉华河上,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
公允地说,哈维对爱因斯坦大脑如此固执而热衷,并不完全为了名气,更不为金钱——他曾经多次拒绝高价购买这些大脑样品的要求。哈维一直恪守对爱因斯坦一家的承诺,在自己后半生里尽了最大努力,希望能用科学的方法解读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密码。大脑一被固定,哈维就对它进行了仔细的测量,还从各个不同角度拍了许多照片。根据哈维的测定,爱因斯坦的大脑重为1230克。与人们对天才的期望不同,这个重量在七十多岁的老年男性里,也不过是一个较低的数值。
在哈维被解职后不久,他就将大脑带到费城医院,在那里,经过严格训练的技术员遵照权威的大脑解剖图谱,把这团珍贵的中枢神经组织小心翼翼地切成了两百四十块。某些脑块又被进而切成薄片,固定在玻璃片上。哈维一共制作出十二套这样的脑片标本,随后,他把这些标本寄给当年神经界最有名的科学家,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惊动世人的发现。剩下的组织被包裹在透明的火棉胶里,悬浮在充满甲醛固定剂的大玻璃瓶中,从哈维家的地下室到办公室的纸板盒里,它们静默了整整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间,除了偶尔被科学家宣布无论是大体形态还是神经细胞的数量都“与普通人的大脑没有什么区别”以外,这些独一无二的神经组织,没有引爆任何科学发现。
甚至,其间唯一的新闻轰动,只来自于爱因斯坦本身的名气。1978年8月,《新泽西月刊》的记者史蒂夫·利维(Steve Levy)辗转找到哈维,当装有爱因斯坦大脑(和小脑)的玻璃瓶出现在利维面前时,他“完全失去了语言”,充满震撼和崇拜地望着那些在清澈的固定液中上下起伏的“花生糖棒”般大小的脑组织块——“那仿佛是宗教般的经历”,史蒂夫后来写道。他的文章立刻将新闻界推向癫狂,许多记者在哈维的办公室外安营扎寨,把他的生活搅动得沸反盈天。当然,即便焦点是爱因斯坦,随着时间的过去,猎奇的狂热也渐渐平淡。而那些不平凡的组织块,依然寂寞地在玻璃瓶中沉浮。
与众不同的大脑?
八十年代初的一天,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玛丽安·戴蒙德(Marian Diamond)坐在丈夫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只能独自思考”。近二十年前她发现,如果把小鼠养在有各种玩具的环境中,它们脑中神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的比例将比那些饲养在普通环境里的老鼠要高。她认为,神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提供养料,它们的比例增高正暗示着养在内容丰富的环境中的小鼠神经活动更为活跃,需要更多的营养。在这个无聊的下午,戴蒙德想到了实验室墙壁上不知哪个研究生贴上去的对哈维的报道,突然意识到,她也许可以向哈维索取一些样品,也许这颗不同寻常的大脑里,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也比常人高呢?
说据戴蒙德说,她每隔六个月就要打电话骚扰哈维一次,坚持了三年之后,哈维终于寄给她四块“方糖大小”的脑组织。她的实验结果在1985年发表在《实验神经病学》上,她将爱因斯坦的大脑和十一位普通人的大脑进行对比以后,发现位于左侧顶叶的那块标本里,爱因斯坦的大脑中神经胶质细胞的比例确实比其他人要高上一倍。她据此推论说,“这一现象显示了爱因斯坦在展示他非同寻常的理性思考能力时,这一脑区的活动得到增强。”
哈维渴盼已久的科学发现姗姗来迟,媒体掀起新一轮爱因斯坦狂潮。可是,这份研究报告在科学界饱受争议。日本大阪生物科学所的堪沙博士(Sachi Sri Kantha)对戴蒙德所用的十一位“普通人”大脑提出质疑:这是些什么样的普通人?怎么死的?爱因斯坦终年七十六岁,为什么选取的这十一人平均寿命只有六十四岁?较高的胶质细胞比例是不是只是因为爱因斯坦的神经细胞在衰老过程中死亡更多?纽约佩斯大学的海因教授(Terence Hine)更直言不讳地说:“这项研究充满了谬误,其结果根本不可相信。”
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一纸传真出现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教授桑德拉·维特森(Sandra Witelson)的面前,上面是一个简洁的问题:
您愿意和我合作研究爱因斯坦的大脑吗?
托马斯·哈维
维特森并不认识哈维,但也许是由于爱因斯坦这四个字的魔力,她抄起一张白纸,写上“Yes”,传真回去。
维特森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大脑标本——从1977年到1987年间她设法说服了120位癌症晚期病人捐献他们的大脑。她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许多高水平的学术杂志上。最出名的,也最富争议的,大约是她对男女大脑结构的比较。譬如,她发现在大脑颞叶里一块主管语言的区域,女性的神经元密度平均比男性要高出 12%,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通常女性更善于交流。
这是1995年,八十四岁的哈维读到了维特森的文章。他想,自己也许终于等来了那个能解开谜底的人。得到维特森的肯定答复后,年迈的他小心翼翼地把装有爱因斯坦大脑的玻璃瓶放在他破旧的道奇车里,一路向北,驶过美加边境,亲自将它带到了维特森的面前。
维特森最后挑选了十四块样品,哈维还从来没有给出过这么多的大脑样品。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最重要的发现却不是来自于对这些样品的直接观察,而是源于1955年哈维给这颗大脑拍摄的照片。
维特森发现,爱因斯坦的顶叶下部的区域比一般人宽。而且,一般人的大脑里有一条叫做“外侧裂”的脑沟穿过这里,沟的尾稍劈入一块名为“缘上回”区域。而在爱因斯坦的大脑照片上则显示,他的外侧裂在进入顶叶下部区域之前就与另一条脑沟合并,缘上回也显得更为完整。维特森认为,一般情况下,大脑中神经连接密集的地方形成凸起的脑回,而神经连接比较稀少的地方则凹下变成脑沟,爱因斯坦戛然而止的外侧沟,正反应了他顶叶下部区域比一般人神经连接密集。
维特森的研究显然比戴蒙德的更受礼遇,1999年,她的结果发表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
直到今日,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研究依然不时浮出水面。就在今年五月四号,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迪安·法尔克(Dean Falk)在《进化神经科学前沿》(Frontiers in Evolutionary Neuroscience)上发表了他的最新研究结果。他对爱因斯坦大脑的照片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脑回和脑沟结构。他宣称这颗大脑的结构中含有许多不对称的成分,而很可能正是这些变化多端的沟回,造就了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天才。此外,他在爱因斯坦的右侧运动皮层里发现了一个特殊球状的结构,这在其他音乐家的大脑中也有发现,很可能与爱因斯坦从小接受的小提琴训练有关。
顶叶天才?
由于这些实验都指向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顶叶,“顶叶天才”这样的名号开始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那到底顶叶在哪里,有什么作用呢?
举起你的双手,分别放在左右上耳廓的后部,贴着头皮将手移向后脑勺顶最突起的地方,在哪里汇合。你的双手刚才触摸过的头骨之下的这片区域,差不多就是顶叶之所在。而维特森所发现的爱因斯坦大脑中比常人更宽的下顶叶,在这片区域的后部偏下的地方。这里是视觉、听觉、体觉(来自身体各部分的感觉)、和前庭器官的神经通路的交汇处,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人体综合各种感觉,产生更高等的神经、认知活动的地方。这片脑区主管着视觉空间认知、数学能力和运动想象能力。如果顶叶受伤,病人将无法完成一些复杂的会话、阅读和定位活动。
作为史上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超凡的抽象能力无可置疑。而他曾经说过,自己几乎不以语言文字的方式的方式思考,而是像放电影一样用图画般的想象力来思考问题,这与下顶叶的想象与空间认知功能遥遥呼应。进而,维特森等科学家推论,由于爱因斯坦的下顶叶扩大,影响了领近区域主管语言的Broca区域的发展。而爱因斯坦三岁才会说话的事实,大约已经家喻户晓了吧?
可是,这块不过三指宽的区域真能解释爱因斯坦的传奇成就吗?科学家们纷纷质疑。有人指出爱因斯坦中学时在画图和地理课上成绩平平,与有一片发达顶叶的事实相左。而且,顶叶宽大者大有人在,最明显的莫过于早年失明者。因为他们不再能接受视觉信号,所以顶叶的功能区域一直延伸到通常用来处理视觉信息的枕叶。如果顶叶扩大就能成就爱因斯坦,盲人学校早就成了诺奖基地了。
另外,新英格兰医学院的教授弗德里克·莱波雷(Frederick Lepore)指出,人不会一成不变,对一颗七十六岁的老龄大脑的研究,是否能解释二十六岁以相对论震撼世界的那位年轻人的非凡神经活动,实在令人怀疑。实际上,即便我们能窥探到青年爱因斯坦的大脑沟回形状,就一定能从中分析出他的智慧能力吗?现代神经学已经深入分子水平,发现了记忆和学习中重要蛋白质的改变,而这样的变化,又岂是盯着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切下的“方糖块”就能发现的呢?就连维特森本人也在文章最后说“显而易见的,这份报告并不能解决长久以来神经结构和智力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2007年4月5日,九十五岁的哈维在普林斯顿去世,在同一座城市里,爱因斯坦的大脑依旧储存在病理学实验室的地下室中。五十二年前,当他亲手取出的那块传奇的大脑时,他希望能借此窥探伟大的智慧缘自何方;而在他去世的时候,神经科学的发展已经远远突破了他当年所能想象的一切。然而,他所等待的开启天书的那把钥匙,却始终不曾出现。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可是,直至今日,任何关于爱因斯坦的大脑的研究都能掀起一阵旋风,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停止。也许正如美国教授史蒂夫·王(Steve C Wang)在《科学》杂志上所说:
“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些检验,以及我们想从中得到什么。正如爱因斯坦以他著名的公式捕捉到能量和物质的精髓,我们则在试图捕捉天才的精髓。而我们的这些努力,与其说挖掘了天才的本质,倒不如说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