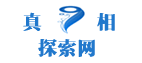解放军的防空体系承袭自苏军,两者都主要依靠地面引导,当年的实际拦截半径基本也都是200公里。256号飞出的航线,只有一小段穿过赤峰的空1师拦截区(最短距离约144公里)。而对于驻蒙苏军来说,则是“可望而不可及”!
关于256号的航线选择与中苏蒙防空体系的关系,如果舒云等非航空专业的研究者没有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但康庭梓和时念堂作为34师的飞行员和师长,包括当时空指的参谋人员,他们在回忆录中没有说明,这就应该是故意回避了。
三、“问号”之迷?
256号的航线选择,也引出了另一个疑问:这条航线是谁确定的?
解开这个疑问前,先要回过头来看一下256号起飞阶段的“问号航迹”之迷。
先回放一下起飞阶段海军山海关场站的雷达监视记录:
“零点36分,航向244度。”
“零点40分,航向270到280度。”
“零点43分,飞行航向290度。”
“零点46分,航向310度,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500多公里。”
零点46分,256号飞出山海关雷达监视范围,目标消失。山海关雷达监视时间共14分钟。
之后256号在迁安县(现河北迁安市)空域,又进行了航向转弯,转向了340度并飞行约4分钟,再转关于256号起飞阶段的“问号”飞行航迹,也是“913事件”分析中关注较多的。在各个版本的描述中,有些还加入了很多的感情色彩。其实,这个“问号”之迷,只要从飞行知识来分析,是很好解释的。
将各时间点的航向延伸就可发现:零点40分时选择的270~280度航向直指北京。零点43分转向290度,这个方向是张家口方向。零点46分转向310度,这是二连浩特方向。
当时华北飞外蒙或苏联的国际航线正是从北京开始,经张家口、二连浩特过境入蒙,再经赛音山达、乔依尔到乌兰巴托。不过至少到9月13日凌晨零点05分前,潘景寅只知道是飞广州。所以256号准备的航线只有北戴河-北京和北戴河-广州,加上潘景寅之前有数次飞伊尔库茨克的经验以及专机机长的资料配备,不排除有北京-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但,肯定没有的是,北戴河至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所以飞机在起飞后第一个转弯先转向了北京,这是必须的,无论是回北京还是飞苏联(外蒙)。
-
飞行需要领航,这完全不同于开车。开车找不着路可停车确定方位,但飞机不可能。飞机一旦升空,每分每秒都在快速运动(快速改变位置),每分每秒都在消耗燃料,而且耗油量在不同的高度、速度下都不一样。正常的情况下,飞行员都是在升空前做好飞行计划,在航图上画好明确的航线,“三叉戟”这样的大型飞机还需要配备领航员。同时在升空后还要依靠地面管制站的引导,以及地面导航台等设备来校正航向。
但这些条件显然在9月13日凌晨256号升空时是不具备的,没有副驾驶、没有领航员、没有航线图、没有导航台、甚至油料也没加足。那么起飞后,当得知飞往伊尔库茨克后,256号就必须重新计算航线,而此时飞机已经升空了!这时的256号若想重新计算去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只能依靠原始的领航方法,靠地标导航,用航位推测法计算新航线。
地标导航首先要找检查点(地标)。在这个“问号航迹”上:
·256号第一个转弯后飞经的是抚宁县,并飞过抚宁县约有1分45秒,这个阶段的航向是270~280度不稳定的。说明此时飞行员在计算航线,并寻找下一个检查点以校对位置。如果此时航线确定是北京,256号会维持这个航向直到下一个检查点。但以当时的情况看,256号肯定不能飞北京。若走完整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256号的燃料连乌兰巴托都飞不到。
飞过抚宁县1分45秒后,开始转向290度,这时飞经的是卢龙县,过卢龙县又飞了约1分钟。这个阶段飞行员可以校正之前计算的误差,也可以计算最终的路线。维持这个航向是张家口,是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的第一个捷径。但这同样也不可取,一是燃料很够呛,二是张家口是空7师防空重地。256号取张家口方向无疑是往枪口(导弹阵地)上撞,甚至是在“调戏”中国空军。当天周宇弛一伙的3685号便是强闯张家口,走了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遭到了空七师歼击机的拦截。
·过卢龙县1分钟后,转向310度,飞往迁安县(现迁安市)。这个航向直指二连浩特,这是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在中国境内最后一个导航站,但同样没有选择。取这条航线,虽然基本不会飞入防空导弹的伏击圈,但也很长时间处于空七师的歼击机防空圈内,这是比较危险的。即使安全飞出境后,也将直接撞进蒙军和苏军的防空圈(根据资料,蒙军当时有防空导弹沿此线布署)。
——以上三段飞行转向,基本都是在靠向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的每一个检查点,在导航中类似于“狗追兔子法”。
·在迁安县上空256号转340度航向,飞行了约4分钟,这一段340度飞行长期以来被很多人不解。
曾有民间的研究者认为是为了“迷惑林彪”,让林彪察觉不出是(西)北飞苏联。这一观点是缺乏飞行专业知识的。如果飞机的航线已经确定,航线转弯是以秒为单位的。究竟转了多少度?转向了哪里?这只有飞行员看着仪表才清楚,乘客(林彪)是根本确定不了的。更何况256号是在燃油吃紧的情况下升空的,节约燃料是首当其冲的。
而飞行专业出身的康庭梓和时念堂则表示,“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载于《航空知识》2002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时念堂,《解说林彪叛逃的四大迷题》,载于《民主与法制》)。不过笔者倒不认为康庭梓和时念堂这样的优秀飞行员会真的不明白。
事实上,转340度飞行4分钟说明此时256号已经确定了经承德-温都尔汗的最终航线,向最终航线上作调整飞行。这是飞行中调整航向的基本动作。
·过迁安县后飞4分钟,256号转向325度航向,此航向的下个检查点是承德市。如果飞行员计算准确,256号将飞过承德上空,而后保持航向即可——事实上256号做到了,飞机准确的经过了承德市正上方。之后256号就再没变过航向,直飞外蒙。
整个“问号”飞行共用时约18分钟。扣除310度转340度这段调整飞行,是14分钟。再扣除起飞爬升时间,是10分钟。这意味着,256号是在起飞后的10分钟时间里,完成了飞行中重新计算新航线的工作!这一切是在维持3000米飞行高度、夜间目视条件差、没有副驾驶、没有领航员、没有地面导航站的条件下完成的。
排除掉一切如“是否叛逃”、“机组是否抵制”、“机组是否有思想斗争”等假设因素,即使是在白天,让另一个建制完整的机组,来重演这个飞行中10分钟重新计算航线的工作,很可能都不容易办到。但是,潘景寅却神奇般的做到了。
四、谁确定了这条航线?
256号的这条航线,准确穿过了华北、东北航空兵防空圈间隙,又正对驻蒙苏军的防空圈间隙。能做出这一选择的人,不仅要懂得飞行知识,还要熟悉中蒙苏的空防军情。
在当天,256号机组只有机长潘景寅和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三个机械师上了飞机。加上学习过飞行基础知识的林立果,最多只有五个人了解飞行知识(无论多少)。而从空防军情的掌握上说,只有潘景寅和林立果有条件掌握的如此详细。潘时任专机师副政委,专机飞行员。作为首长专机的飞行员,他必须随时掌握各地的空防军情,尤其是蒙、苏的军情(因为有出访需要)。而林则是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也理应熟知我军和外军的空防布署。
那么这条航线会不会是林立果之前就准备好的呢?——答案是肯定不可能!
因为,确定这条航线的人,除了要有飞行知识和熟悉军情外,还要知道256号当天的实际飞行能力——油量!
当天周宇弛等人劫持3685号直升机,即是拿出了北京-张家口-二连浩特-乌兰巴托的航线。这说明林立果一伙完全有可能计划过航线,也有条件准备过航线。不过,林立果和周宇弛还属于飞行“菜鸟”级,选择的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也完全是条“找死”线路。
最关键的是,林立果并不知道当天的256号只有12.5吨的燃油。
-
从256号先选择北京、再改张家口、再改二连浩特、最后改向承德这段过程来看,林立果是有很可能给了潘景寅预先准备好的飞往蒙、苏的航线图。但这都不现实,飞机的油不够,还直直的撞向导弹阵地。所以航线在空中被改了,改成了一条谁都难以拦截,也能够飞到乌兰巴托或温都尔汗的航线。
这个改动人,只能是老手,机长潘景寅。
当然,潘在零点05分接到林立果电话的时候,他就可能已经知道了真实目的地,做了准备。但这也只能是初步的飞行计划,此时的潘景寅要忙于256号一系列的起飞准备。最终的航线应该是在起飞后边飞行边计算修正出来的。所以也才出现了许多人困惑的,起飞阶段用了十多分钟才完成最终航向转弯这一现象。
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难以接受潘景寅在主观上配合林立果一伙的结论。认为潘景寅的是被蒙骗的,是被迫外逃等等。
比如当事人康庭梓描述为,“从起飞航向转到270至280度这段艰难迟缓的航迹,我认为是反映了潘景寅操纵飞机转弯时的犹豫与心理上陷入极端困惑的写照。”“开始时机组受蒙蔽”“潘景寅竭力错开北逃航线 ”“他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对涉及空防和国境线等因素也是很敏感的,他肯定对空中叛逃的行为深恶痛绝。现在,他却被命令飞出国境,实行叛逃!”(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载于《航空知识》2002年)。
对于康庭梓的描述,笔者认为明显是一种事后说辞。
·林彪当时是“副统帅”,林副统帅要紧急出国——难道出国就是叛国嘛?!
·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统帅!”(叶群在山海关机场登机前语)——难道你有意见嘛?!
·潘景寅是二号人物的专机机长(毛不乘飞机,林彪实为乘专机的一号人物),送首长出国是家常便饭——难道首长出国前还要你机长来验明是否“叛国”嘛?!
·当年西哈努克长期在中国避难——难道西哈努克飞到中国也叫“叛国”嘛?!
其实若让康庭梓和时念堂来面对当时的情况,以专机飞行员的职责,笔者相信他们也一定会“誓死捍卫林副统帅!”的。
还有人是以邓小平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以及总政1981年12月23日下发潘景寅《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为依据,证明潘“没有问题”。
这些都还是标准的中国思维,非“好人”即“坏人”,非“同志”即“敌人”的传统观念。
其实,评论潘景寅,大家大可不必这样感情色彩。要把他放回到40年前的首长专机机长的身份下,他果断出色的履行了他的职责。在突发情况下随机应变、超水平的完成了一系列看似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强行起飞到空中计算航线,到最后的迫降,潘景寅的表现完全堪称“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