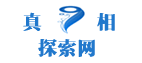土家族历史之迷
思南土家族少数民族汉族武陵山
土家族历史之迷
——土家族发展特点浅谈
张不通
高山、峡谷、古城、纤道、哭嫁、跳傩、戴白帕、对山歌,走进武陵山区,这块以奇山、奇水、奇洞、奇树而甲天下之美的神奇土地,仿佛走进了土家民族发展历史的画卷。
土家族世居武陵山区,历史上长期以火耕水耨、渔猎山伐为业,在与汉、苗等族杂居中,和睦相处,共谋发展,对推动贵州建省、开发武陵山、抗击外敌入侵、支援红军长征、建设黔鄂湘渝四省和睦边区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武陵山繁衍生息的各少数民族中,土家族的人口最多,有800多万,占整个武陵山区2300多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唯一的一个人口超过100万,却聚居于中国中部而非边境位置的少数民族。
经过岁月的雨打风吹,直到1956年12月,土家族才正式被国务院批准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1957年1月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土家族”。那么,穿过数千年的历史迷雾,土家族在发展过程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对此,《嘉靖思南府志》引述了《寰宇记》中关于“思南府”条目中的话,作了概括性描述:“(思南)在荒徼之外,蛮獠杂居,言语各异。居郡东南者,若印江,若朗溪,号曰南客,有客语,多艰鴃不可晓。郡西北,若水德、蛮夷,若务川,若沿河,号曰土人,有土蛮稍平易近俗,而彼此亦不皆同,惟在官应役者为汉语。今人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素所服习。”
这段话说:“思南在很遥远的边疆,少数民族杂居相处,语言各不相同。住在郡城东南方向的,如印江、朗溪,叫做南客,有自己的语言,外来的人都听不懂。住在郡城西北的,如水德、蛮夷、务川、沿河等地,自称土人,这些土著民族的风俗大致一样,但彼此之间却又不完全相同,只有在官府中工作的人会说汉语。现在他们互相交住的时候,说话都和中原相同,是因为他们平时经常学习运用的缘故。”这段话概略地介绍了古代思南地区土家民族的语言、风俗变化、地理分布情况。“蛮”、“獠”、“南客”、“土人”等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对土家少数民族的蔑称。这里所说的“在荒徼之外”,是指思南的地域位置。《尚书》中有一篇介绍中国远古地理状况的文章叫《禹贡》,它把中国疆土分为不同层次的五个地域,名为“五服”:甸服是王城所在的中心区,侯服是中心区周围由中央统一管理的近中心区,绥服是王朝开辟的新区,要服与荒服是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荒徼之外”是说地处武陵山区的思南,是属于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外的地区,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比边疆少数民族更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源 流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土家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这是土家族发展历史的第一个特征。
春秋战国以前,土家族的祖先就在武陵山这块土地上狩猎渔牧,开垦耕耘,生息繁衍,经历了巴——夷——蛮——土——土家的演变过程,至今土家族群众还在唱着“自古地盘是我开,绿树成荫是我栽”的山歌,世世代代扎根武陵山、扎根思南,开发建设着这片美丽的土地。
在耕耘播种、生息繁衍过程中,土家族逐渐形成了与汉族、苗族、仡佬族等各兄弟民族一起,在武陵山大范围内交错混杂居住的大杂居局面。在村寨小范围内,则多是同姓同祖的单一民族聚居,并多以姓氏作寨名,还留有民族政区特征的“洞、峒、司、溪、寨、坝”等遗迹的情况,至今思南县还有160多个村寨属于这种情况。
据1995年统计,铜仁地区有土家族95万人,主要居住在沿河、印江、德江、思南、江口、铜仁等6个县市,分别占了各县总人口的51%、50%、60.6%、26.5%、30.2%和17%。其中,有42个乡镇土家族人口占全乡镇总人口的50%以上,占了全区168个乡镇的25%,有38个乡镇土家族人口占全乡镇总人口的30%以上,占了全区168个乡镇的22.6%。
从思南县27个乡镇的情况来看,土家族人口占全乡镇总人口的50%以上的乡镇有东华、凉水井两个,占30%以上的有枫芸、许家坝、大坝场等14个乡镇。塘头镇4万多人中,汉族占了53.97%,土家、苗等7个民族占了46.03%,两者比例相差不大,是典型的大杂居局面,但川峒、仁和、白鱼村则分别是彭姓仡佬族、张姓土家族、余姓蒙古族的聚居地。枫芸土家族苗族乡1万5千多人中,少数民族为41.51%,并不占绝对多数,但金星村塘池坝、蒙家等自然村寨却分别是张姓土家族、蒙姓苗族等的聚居地。再如冉姓土家族群众,从重庆市酉阳地区搬迁到思南后,散居各地,与各兄弟民族共同杂居相处,但他们又主要在枫芸、溪底、天桥、三溪、磨溪、张家寨、四角、沙沟等较小的地域内聚族而居。
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人口的流动也在逐步加速。有的土家族群众在武陵山、在思南境内住了无数代人后,仍然因为就业、婚姻、战争等各种不同的原因,踏上了流移搬迁的旅程。如枫芸乡冉姓土家族群众从重庆市酉阳地区迁徙而来后,经过了几代人的繁衍,到民国末年,有一支又搬到了凤冈县境内居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双向流动的步伐大大加快,来武陵山区经商、工作的外来人口增多,读书、打工、就业外出的人数猛涨。2000年人口普查时思南县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有54万多人,按户籍人口老口径(即居民的户口还在思南县)统计则是近62万人,即就是有7万多思南土家族等各族群众常年在广东、福建、贵阳等外省市县工作居住,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户籍虽然还在思南县,但已很少回思南了。这还不算近些年已经把户籍搬迁出去的那部分人,更有极少数人甚至已经远涉重洋,到了美洲、欧洲、澳洲。
融 合
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展史是一部大融合、小同化的历史,表现为在与苗族等各少数民族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共同逐渐融合进汉族,而汉族也有被土家族等少数民族部分同化的趋势。这是土家族发展状况的第二个特征。
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张姓、田姓、杨姓等土家族族群众的情况就是如此。思南最大的土司田氏,从隋开皇二年(582年)田宗显入黔为黔州太守,其十四代孙田佑恭为思州蕃部长,宋大观元年入朝内附为思州刺史起,直至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废除田宗鼎的思南宣慰使职务止,始终世袭思州、思南等地土司职位,经历了隋唐五代、宋元明,入黔近千年,世袭土司职位七八百年,其子孙也生息繁衍成为思南土家族大姓。
再如土家族张、杨姓。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张姓第128代传人,陕西咸宁人张恢奉命率兵自川入黔,征剿思州各少数民族,因功封为亚中大夫。他死后,当地少数民族“复叛,恢子焕以计战退”,因功“授焕思州宣抚同知(《道光思南府志》)。”张焕的五个儿子也各被封为思南、印江、铜仁、沿河、万山等地土司,统治当地各族民众。此外,还有杨姓,其入思始祖杨再思在唐咸通十四年(873年)带兵到贵州征剿少数民族,他们的后代也受封为思南等地的大小土司,世代定居下来,其子孙生息繁衍成为思南土家族大姓。如张姓就有6万余人,占思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他们本来是汉族,由于初来时,人口少,又长期与少数民族互通婚姻,生活习俗互相影响,“入夷狄者,则夷狄之”,自身被武陵山土家族同化,就成为土家族的一分子。从历代封建王朝对他们的态度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明万历三十三年九月(1605年11月),专管组织工作的吏部向皇帝报告说:“贵州思南府水德长官司正长官张辂(张恢七世孙)年老乏嗣,本房子孙张治贵,二房子孙张治安争继,多年未有定一。据称治贵非的(嫡)派,治安广行财贿,二房均难承袭,似应于三房张相子孙择其长者袭之,以守先绪。但思南为黔中首郡,文风渐盛,华民日繁,以夷官治华民体统实不相称。抚按二臣议改土设流,深得用夏变夷之意,合无将水德长官司改为县治……(《神宗万历实录》)”。明朝廷认为,思南水德司张家的子孙是夷官(少数民族长官),让他们继续来管理华民(汉族)“体统实不相称”。因此,要改民族自治地区(长官司)为中央定期派出官员进行管理的县,派不能世袭的汉族官员去当县长。
到了明朝永乐、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汉族人由于战争、灾荒、经商、当官、做工等原因大量进入思南,在明朝《嘉靖思南府志》中有很清晰的表述:“府旧为苗夷所居……弘治以前,川民不入境……弘治(1487-1505年)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各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拾遗志》)。”“思南府与川东、重庆、播州、酉阳等处接界,中间山溪平壤,连延千里。每遇荒年,川民流入境内就食。正德六年(1511年),流民入境数多……今年(1537年),流民入境者,络绎道途,布满村落,已不下数万(田秋《陈愚见以备遗策疏》)。”
这说明,明代以前,包括思南在内的武陵山区还完全是土家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汉族人大量进入,不但人数很快超过了各少数民族,而且带来了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步伐开始加快。当时的汉族人“有的择地聚居,有的与当地土著杂处,互通婚姻,生活习俗相互借鉴(《思南民族志》)”。受此影响,“思南之地渐被华风……婚娶礼仪,服饰体制多与中州同(《嘉靖思南府志》)”。再加上汉族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岐视政策的强化作用,现在思南等武陵山区的土家族群众在部分保留本民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大都改为通用汉语、汉文,穿汉族服装,认可汉俗了。
管 理
中央对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民族政策经历了郡县——羁縻——土司——府(县、长官司并存)——州县(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阶段,民族识别也经历了承认——否认——承认的过程。这是土家族发展状况的第三个特征。
历代封建中央王朝在实施统治的过程中,大多采取既团结又镇压的控制政策,根据情况的不同,推行不同的郡(府)县制度、“羁縻制度”或“土司制度”。
秦、汉帝国消灭了武陵山地区的巴、夜郎等少数民族政权后,设置了巴郡、黔中郡、武陵郡、建宁县等地方政权,建立了郡县制度,把这块地区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统治范围。但到了两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地区政治腐败,政权频繁分裂更替,根本无力顾及边疆,于是地方少数民族首领乘机培养势力,主动以形式上的归附,换取并借重中央王朝的封号,提高自己的地位。就在这种中央王朝和地方少数民族首领各得其利的情况下,“羁縻”、“土司”这两种“一国两制”的政策诞生了。在这种背景下,武陵山各地也先后建立了涪川郡、思南州等羁縻州郡,思南宣慰使司、酉阳宣抚司、水特姜长官司等大小土司。
“羁縻制度”又叫内附制度,是南北朝、唐、宋时期封建中央王朝为了巩固边防,维护国土统一,缓和民族矛盾而采取的一种间接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设置都督府或州县,任命当地的土著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等地方长官,子孙世袭,在本地区有军事、刑事、民事等自主权,对中央政府则有进贡及出兵助战等义务。“土司制度”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是元、明、清中央王朝根据各少数民族首领所占据的地盘大小,建立宣慰司、招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和一部分土府、土州、土县,分封少数民族首领充当地方政权机构中的长官,世袭掌权,统治当地人民的民族自治制度。这种“以夷治夷”的统治政策,在当时有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的作用,同时也保留了很多不利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因素。
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和经济的发展,土司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影响民族团结进步的封建领主农奴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王朝废除了思南、思州宣慰使司这两个土家族地方政权,开创了明清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的先例。从明永乐皇帝开始在思南试行“改土归流”政策,到清朝末年的约500年里,中央王朝采取文武并用的措施,逐步废除了武陵山区的土司制度,实行了由中央王朝派遣官员的流官制度,设置了府、县等地县级政权,使土家族地区的地方政权制度与内地完全趋于统一。到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尊重土家族的民族意愿,在1957年1月正式确定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先后建立了恩施、湘西等2个土家族自治州,长阳、五峰、沿河等24个土家族自治县(其中,有5个是单一的土家族自治县)。这是在各民族全体人民翻身作主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族自治政权,与家天下的封建土司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于武陵山土家族的少数民族身分,各封建王朝直到清初一直都是承认的,不管是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汉族官员,还是委任少数民族首领当地方政权长官,都承认这里是“蛮夷之地”,蔑称他们是 “土巴佬”、“土蛮子”等。封建统治者在逐步削夺土司权力的同时,对土家族等各少数民族群众也采取了血腥剿杀的高压政策,特别是明清政府强力推行“改土归流”、“赶苗拓业”,使土家族惨遭荼毒、人口急剧减少,留下了“官占坪,民(汉族)占坡,毕兹卡(土家族自称)被赶进山窝窝”的辛酸记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镇压贵州土官的反抗后,于雍正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清世宗报功说:“此番出师……前往临阵杀敌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者已万人,擒获搜讯明枭首及剁去右手者已数千人,所获……男女分赏在事有功者亦数千人,准于安插并暂准投诚者亦数万人(《朱批谕旨鄂尔泰奏议》)。”
当然,尽管“改土归流”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处于奴隶制经济的民族地区实行血腥镇压才实现的一场社会改革,但它毕竟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扫除了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迅速改变了思南等地土家族地区的土司“禁民居不得瓦屋,不得种稻,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的野蛮落后状况,使新设流官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原土家族地区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形式与内地完全划一,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西南边疆的巩固都有着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正如清末大思想家魏源在《西南夷改流记》中所说:“人即不革之,苗亦必自大变动,以大更革之。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正因为如此,才使武陵山的思南地区出现了“一时之创夷,百世之恬熙”的局面,比西藏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提前进步了五百年。
但是,思南境内的土家族人在从清中叶到民国后期的一百多年中,却因此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少数民族成分,上层统治者也否认了思南境内存在少数民族的事实。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杨森接任贵州省主席,他以法西斯手段推行“中国化运动”,提出“今宜公认中华民国境内,只有一个国族,一个领袖,以坚强国民之信念,而实现孔子大一统之理想。故凡吾国国人,必须在思想方面确定一种信仰(即孔子大同学说,蒋介石总裁言论);行动方面,则为统一中华文字,推行中华语言,划一种服装,由尚同以跻大同之声(《贵州近代史》)”。十月二十二日,思南县长李剑青在大力推行省政府“严禁各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文字,穿自己的服装,过自己的节日,如有违背禁令,分别给警告、罚款”的“中国化运动”,实施大汉族同化政策后,向县参议会第四次大会作了施政报告,强行宣布:“境内均汉族,并无其他民族杂处其间。”
这样,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歧视和同化政策,给解放后的民族识别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1954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思南县只上报了松桃籍干部田兴国夫妇二人的苗族成分,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仍只上报了外籍人因工作或婚姻迁入思南的217人的少数民族成分。
1983-1984年,在土家族群众的强烈要求下,根据中央的文件要求,思南等尚未恢复土家族身份的武陵山各县,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了民族识别恢复工作,采取一个乡一个村地对照史料、族源、血缘等历史记载的方式,根据现实风俗习惯等特征,认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了土家族群众的民族身份。如思南本地250多个姓氏中,就认定并恢复了张、杨、田和外地来的冉、任、周、李、陈姓的部分群众为土家族。当然,由于渊源不同,同姓不一定同族,如枫芸乡塘池坝村张姓认定为土家族,县城思唐镇所辖的阁老寨(即过去的仡佬寨)和凉水井镇泡木寨村的张姓认定为仡佬族,息乐溪张家山、周家山等地的张姓则认定为苗族。
特 色
解放以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土家族的语言、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特征快速消失,土家族与武陵山各民族自愿融合的速度在加快。这是土家族发展状况的第四个特征。
土家族有着自己古老的独特的民族特征。西周时期,土家族的祖先巴人在川渝鄂边境一带建立了巴国。公元前788年,巴楚两国发生战争,巴国为了巩固后方,开辟并占领了乌江中下游。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楚庄王称霸,楚国势力逐步从鄂西扩张到湖南沅江中下游及其支流锦江流域。巴国为了抵制楚国的势力,更加努力于乌江中下游流域的巩固,占领了乌江中上游鸭池河、六冲河、三岔河流域(《贵州上古政区》)。到了公元前315年,秦国灭巴国设巴郡时,贵州高原和武陵山区始终直接受到巴蜀文化的洗礼和荆楚文化的熏陶。直到明朝改土归流后,汉族人大量来到武陵山区止,虽然有一些中央政府部队过境,但时间短、人数少,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使这里仍保留着很多巴楚先民的原始风貌。
据《嘉靖思南府志》记载:“风俗,本府同黔中地,在荒徼之外,蛮僚杂居,言语各异,渐被华风……信巫屏医,击鼓迎客,刀耕火种,务本力穑,唱歌耕种,以泥封门,得兽祭鬼。”这里说的就是明朝时期的思南土家族地区的风俗、民族、语言情况,说明当时思南是“各民族杂居相处,语言各不相同,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平时相信巫术,拒绝医生,敲鼓奏乐迎接客人,砍树烧地种植庄稼,唱着歌耕种土地,冬天用泥土封住门窗,用猎物来祭祀鬼神。”
由于明清时期改土归流,设儒学、开科举、兴教化,加上具有先进文化的川东汉族人大量来到思南,使思南“渐被华风”,土家民族风俗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同时,受历代统治者的歧视政策、战争、天灾人祸、迁居杂处等各种历史原因的影响,许多特征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清《道光思南府志》说:“五方风土不同,习俗亦异,浇漓淳薄,举视教化……在上者,三令五申去奢崇俭,郡士大夫力行以为倡率,庶民先克,遂风俗蒸蒸还淳也。”这里说,到了清朝,土家族地区的思南虽然仍旧是各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但由于政府官员三令五申地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教育,地方官宦人家带头作榜样,使普通老百姓也改变风俗,逐渐跟中原汉族地区相同了。
长期的风霜雨雪,终于使武陵山各兄弟民族具有了互相包容、互为表征的多元文化特征。但到了二十世纪上中叶,土家族仍保留有一些别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如“赶年”,体现祖先崇拜的“祭祀土王”,亦歌亦泣的“哭嫁”、神秘原始的“祭风神”,热闹风趣的“打闹”、欢乐祥和的“建房礼词”,以及吸收中原文化并融入本民族特点的“冲傩”、“还愿”等。
因地理环境不同,这些习俗在各地有大同小异的差别。如丧葬,土家族先后经历了岩洞葬、火葬、生基葬、棺木土葬等历史阶段,棺木土葬要经过入殓、奠礼、安葬、祭坟等过程,出殡前要闹丧,要设歌场,唱丧歌、击锣鼓伴唱、打绕棺跳丧等。再如婚俗,一般都要经过提亲、下书子、讨庚、过礼、哭嫁、接亲等几个阶段,女方花园酒(出嫁仪式)时,要给新娘“梳髻”、“开脸”,要摆出嫁妆“亮彩”,新娘及母亲姑嫂、乡邻姊妹要“哭嫁”,接亲队要举行“拦门礼”,新娘离家要“辞祖”。其中,既有土家族自己的“哭嫁”等特色,也烙上了下书、讨庚等汉族文化的印记。
同时,各地土家族群众又各有一些独特的民俗,如思南县枫芸乡的“产油烟”(除夕时,小孩到寨上群众家的地里采菜,第二天听任主人家假骂)、板桥乡的“抬甩神”,在其他乡镇就不存在。不过,解放后受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等现代化进程的冲击,许多民族特征正逐渐消亡,民族融合的步伐在加快,风俗习惯越来越趋向完全统一。
武陵山区土家族本来“言语各异”,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长期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同化运动,土家族群众不得不操练汉语,习用汉文,疏远并逐渐淡忘了本民族语言,通用汉语和汉文。如思南因为川民入境者“数多”,土家族群众更多地保留了四川口音。但从一些地名、称谓或遗音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土家语等民族特征的痕迹。如“思南”这个名称,土家语译音为(cn nkh ph ),意思是闻名中外的“土花铺盖”,城郊的“息乐溪”土家语为(cl tchi )、(cl )是“听见”,(tchi )是“响”,意为“响水”,“息乐溪”即“响声很大的溪水”。再如父亲,在思南境内由“阿巴”发展到现在的“嗲嗲”、“伯伯”、“爹”、“爸爸”等称呼,外祖父也由“母思阿巴”发展到“嘎嘎”、“嘎公”、“外公”等叫法。
土家族的服装也有一定的特色。土家族男子多穿自制土布缝制的5至7排布扣的对襟衣,下穿大裤管白裤腰的抄腰裤,头包7至9尺长的青白布帕,一百多年前,震惊清廷、浴血战斗了十多年的白号军大起义,就是因为起义部队头包地方民族白布头饰而得名。女式服装则为上身大袖口布扣并沿领口及四周均绣有花边的排子衣,下装与男式制作相同,只是沿裤脚绣有花边,已婚女性包5至7尺长的青白布折叠帕,未婚女子蓄有长辫。目前,无论男女老幼服装都已开始潮流化,购买服装代替了过去的自己纺织,皮鞋、胶鞋代替了草鞋,各式帽子代替了青白布帕,除一些中老年男女还保留原着装式样外,大多已穿起中山装、西装、、牛仔裤、连衣裙等时装了。
很早以前,土家族青年婚姻比较自由,多是在节日社交唱歌跳舞时,男女彼此爱慕,并得到土老师作证,就可订亲,婚娶时也不索取任何钱财。随着封建婚姻制度的确立,自由婚姻逐渐被买卖婚姻或变相买卖婚姻所代替。出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肚腹亲”、“背带亲”、“扁担亲”、“姑舅亲”等。解放后,才又有所改变,新式婚俗减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同时,土家族群众还信仰“万物有灵”,认为世上地有地神,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洞有洞神,万事万物都有神,崇尚巫术,信奉土老师,崇拜其驱灾消难的神力。到了清末,受汉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影响,土家族地区形成了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天主教并存的社会现象,但解放后出生的人们已大多不信这些了。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道路交通、邮电通讯、报纸电视、电脑网络的普及,再加上长时期的杂居相处、互通婚姻,汉化程度深,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土家族早就在心理上认可了中华民族这一共有称谓,许多土家族群众对于作为个体的自身属于哪一个民族的身份已经不再执着,认为“都是一家人,兄弟姊妹一样亲”。如思南的安姓群众,虽然其祖先历史上长期为土司头人,并有史书为证,但因为进行民族识别时,自身的土家族民族意识不强烈,只认可汉族意识,所以没有恢复其土家族身份,就被认定为汉族。再如家庭成员由汉族和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同胞共同组成的家庭,为了得到升学、就业等民族优惠政策的照顾,子女常常依附其中一个家庭长辈的少数民族身份,但对其民族内涵却很少作深入了解。
以上为土家族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特点,湘鄂黔渝武陵山土家族地区各县的情况大体相同,只是在不同地方的具体内容上,如民族人口比例、姓氏分布等细节上有所不同罢了。可以同时肯定的是,现阶段武陵山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土家族与各兄弟民族已经“和同一家”,在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道路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经济利益都已经密不可分,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各民族兄弟姊妹携手而行,与时俱进的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团结局面,保证了国土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策法令的顺利施行,赢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进步的中华民族开始全面复兴的新时代。 |